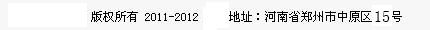12月11日是“木兰的故事”游戏剧场和个人史展开展的第一天,下午接近三点,我们打开悦·美术馆的大门,迎接属于这场展的第一波观众。人们走进展馆,在某一张照片、一份文字、一个物件前停下脚步,看见基层流动女性的故事,这便是最好的时刻。
我们想告诉你,关于这场展的幕后故事,关于这场展ta们看到了什么。
开幕式上木兰文艺队正在表演
Ta说
赵志勇欢迎来到木兰的世界
年至年,木兰社区中心发起了一个社区戏剧项目《生育纪事》。在为创作收集素材的过程中,社区中心一共采访了29名生活在社区里的基层流动女性。阅读这29个生命故事给了我太多的震撼。然而,因为在城边村社区搞创作,资源实在有限,最后我只从中选择了很有限的几个故事来进行排演。戏演完之后,我常常会想起没有被搬上舞台的那二十几位讲述者。我感觉对于她们无条件托付的那份信任,我们欠了一份交待。
《生育纪事》完成之后,木兰社区中心继续针对基层流动女性的生命故事展开社区口述史调研工作。这一次,在北京、广东等地采访了更多的基层打工女性,她们的讲述也不再限于婚恋、生育话题,而是涉及到自己原生家庭、成长经历、职业生涯和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故事,敞开了一个属于基层流动女性的世界。
年春节期间,我阅读了将近四十万字的采访记录。读完最后一个故事的那天夜晚,我走上天台,默默地点了一支烟。我在想:是否有可能不做任何艺术化的挑选、删改和润色,就让这些故事不假修饰的直接呈现呢?如果我们有一个展厅,里面全是打工姐妹们讲述的故事被打印成文字,或者一个个的耳机在播放她们讲述的采访录音片段。那将是一个语词的丛林,打工姐妹们生命经验的碎片在此交织、激荡、回响。这样的一个展览,会有观众愿意走进来,拾取一点他人生命故事的吉光片羽么?
遇到悦·美术馆的策展人成蹊老师之后,这个想法成为现实,甚至变得更加丰富。最终呈现的展览里,不仅有基层姐妹讲述自己生命经验的语词,还有她们各种人生场景的见证,精神生活和艺术创造活动的结晶。欢迎来到木兰的世界,这个展览的策展过程奇妙而独特。社区中心的负责人带着策展人到社区姐妹家中挨个登门拜访,一边聊天一边搜寻征集那些携带着主人的生命经验和故事的物品。那个场景让我觉得奇妙而感动。来自不同生活场景的人们在一个空间相遇,彼此坦然地相互信任,自然而然地开始分享自己的生活。我衷心希望来到展厅的观众们,也能分享到这种亲密友爱的氛围,并且与展品背后那些故事的讲述者们建立起一点信任和分享的关系。
“木兰的故事”是一个很酷的艺术项目。它是一个剧场游戏和一个主题文献展构成的有机整体。玩家们在游戏世界中体验的木兰花的人生,是现实中千千万万朵“木兰花”真实经历的缩影。而现实中“木兰花”们在人生岁月里留下的痕迹,隐藏着游戏玩家们通关的索引和指南。在这里,虚拟和真实互为镜像。
这也是一个有点另类的艺术项目。它和别的游戏不一样,没有升级打怪,没有道具奖励,甚至不太“爽”。在这里玩家所经验的,只是一个打工女性在各种人生情境里可能遭遇的人生盲盒与有限选择。而在文献展中,我们尝试在展览现场还原木兰花们生命经历中的种种片段,没有删改、不加修饰。每一件展品及其背后的故事,都带着一段真实经历的余响。
这将会是一个祛魅的艺术现场。它不粉饰现实,它不承诺未来,它只是记录和再现一群人生命中某些经验的碎片。在当下中国,流动打工女性的总人数已经超过了1亿。她们生命经验中的若干碎片拼在一起,就是我们所有人身处其中的一块巨大而坚硬的现实。
游戏剧场
游戏剧场
丽霞筹备展览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过程,现场有相当一部分展品其实是木兰十多年工作成果的累积,这些年木兰与姐妹们建立起的链接,让她们对木兰有信任,在对这个展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愿意支持这个展览。
这个展充满了不确定性,它并没有一个事先规划好的展品内容,在布展的过程中,我们不停地有新的创意、新的想法。比如有一些展品在我们的生活中会觉得它特别普通,它没有作为常规意义上人们所理解的展品的意义,那怎么确定要用这个展品呢?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展览前,我和策展人成蹊老师、赵志勇老师一起去到社区姐妹的家里,在和姐妹聊天的过程中去发现一个展品背后的故事。
比如在现场的展品里面,我有两个印象特别深的。现场有一个抱枕,它是一个已经离开北京的姐妹用自己拍的照片做成的,在她离开北京的时候,她又送给了她的好姐妹。我们去的时候,这个抱枕就放在沙发上,赵老师一眼认出了抱枕图像的姐妹,这就引出了背后的故事,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展品带到了的悦美术馆。
抱枕、小镜子等物件
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关于推动全家每个成员都应该参与和分担家务劳动的活动,一个姐妹的孩子在参加这个活动之后,制作了一个家务分配器,贴在了家里的墙上,这个展品也是在走访的时候发现的,被看中带到了展览现场。
家务分配器
还有一些展品是在策展过程收集起来的。比如现场会需要一些一寸的证件照,那我们就在群里发动大家来去找自己的证件照,很多姐妹会说,哎呀证件照都没好好照过,很多证件照很丑啊。有的姐妹呢,就会从自己之前的证件上把照片剪下来送到木兰,一些其他的公益机构也帮我们一起收集。
有一次我们突然觉得现场如果能有一些与女性身份相关的展品会更好,那决定收集高跟鞋。我们就想,哪个姐妹喜欢穿高跟鞋呢?谁的高跟鞋会有一点故事呢?我们就会跟姐妹们说,我们这个展览需要高跟鞋,你的高跟鞋愿意不愿意拿出来。布展的头天晚上,她们都把高跟鞋送到了木兰的小办公室里。第二天早上,我就用行李箱拉了一箱高跟鞋去了展览现场。
高跟鞋
展厅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是以这样的方式,从姐妹们的家里“搜”出来的,这些展品有很多都是正在被使用着的。
比如现场的小镜子、凳子、工服、衣架,都是从这些流动姐妹家里取出来支持到木兰现场的。还有一些展品是从外地,打工的地方、他们的老家,寄到了北京。
一些工服
我们也邀请了木兰覆盖范围之外的一些其他流动姐妹的作品,也有一些艺术家们的作品。和他们一沟通,他们都非常支持这个活动,从不同的地方把东西寄过来,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奇妙,这次活动得到了众多人的支持和帮助,非常多的志愿者贡献心力,最后才促成了这次展览。
成蹊策展人长久以来,我们对一个群体的认识,经常停留在数据和概念之中,而鲜活的生命只能通过一个个个体呈现出来的,她们的生命历程是具体可感的。
“木兰社区”作为服务基层流动女性群体的公益组织已有十年之久,她们做了大量的社会实践,并有众多公益人士参与工作令人感动。本次展览的文献和素材都来自“木兰社区”姐妹们的日常生活和创作,无论生命中的暗淡和欢欣都尽可能做到客观、真实的陈述和呈现。展览希望通过对基层流动女性个案研究和呈现揭示生命的复杂性,通过多角度、多层次展开,尽量不被“艺术”所限,努力使各个层面的群体都能有所体悟。
从策展的角度来说,本次展览有意在构成一个“场”。这个场是由展品和观众共同构成的,也就是说没有观众在场的展览是不完整的。现场的互动、表演、观看和展示被看作处境的隐喻。这次展览现场的观众构成非常丰富,有木兰姐妹、工友及家属和孩子们,有艺术家、创作者、社会学者和媒体人,有感同身受的同龄人,有好奇、